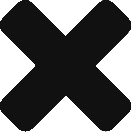站在27歲的路口,轉身回望著自己經歷過的每一場畢業典禮,覺得當年那種真無知、等待引導的狀態很寶貴,卻也很珍惜得來不易的成長經驗。長大最開心的事情是經濟獨立,學會在物質上與情感上承擔自己,也終於下定決心終止長期困擾我的來自家庭的恐嚇與毒罵。過去幾年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夢裡的我同時是個小女孩,也是一位站在女孩背後遠遠地望著她的大人,大人的我慢慢地走向女孩的我,伸手從背後抱住她。醒來以後的我膽戰心驚地盯著天花板,覺得那個夢境像極了我的生命隱喻,有一種跟生命源頭切割了的荒涼感,卻也因為自己救贖了自己而感受到由內在散發的溫煦。
當我們被迫成為一個保護者時,即使還年輕稚氣,也不禁有種古怪蒼老的感覺。那感覺的最深處其實是一個巨大寂寞的空洞,它讓迎面吹來的微風變成冷冽的霜,浮光微塵變成刺痛皮膚的砂子。回頭也沒有退路,因為倒下來的時候沒有人會接住你。
有好幾年,我一直都有這種感覺,好像沒有走好倒下來,就會永無止盡地墜落。長大就是誠惶誠恐地過著每一天,又不再願意回頭。直到這半年我才恍然想起27歲其實還是很年輕,我還有好多新的事物想學習,還有好多還沒有看過的風景。會這麼想的部分原因其實是疫情的持續,在這段期間發展新的興趣的同時也思考著學界以外的可能性。
對我來說,選擇了學界,不只是選擇一種工作型態,更是選擇了一種生活還有價值觀建立的方式,並且在做出選擇以後,可能一直都會待在裡邊,不一定能在其他的專業以及生命場域走動。來唸研究所前還有開始念的幾年,沒有很慎重地思考過這些選擇的意義,那個時候只是執意地希望能夠到離家很遠的地方,獨立過生活,帶著蠢蠢的美國夢。那個時候,也很單純地認為拿了人文科的博士,眼前只有學界的路可以走,因為身邊所有的師長、同事們都是這樣走的,大家都繼續在學界的體制裡耕耘自己的領域與人生。
雖然一直很享受著思辯與書寫、喜歡對話與教學,有那麼一瞬間還是覺得30歲前就要決定自己未來一生的道路與職業,是一個很巨大的承諾。害怕未來自己對於自己、人群、世界的認識都要建立在學術體制上,個人的生命也就跟高教機構綁在一起。
跟朋友們聊著這件事情,被笑說其實去了業界也是這樣,只是綁架你的對象是公司、組織還有各式各樣的職銜。事實好像的確如此,上一週去參加了我們學校的校友職涯服務辦的networking 活動,想要了解學界以外,人文科博士有什麼樣的選擇,結果在談談話中職涯中心的代表跟我說 “You will most likely need to work your way up to big titles–just try to get your foot in the door and prove yourself!” 這句話讓我哭笑不得,事後傳簡訊跟朋友說,怎麼這跟我在研究所裡偶爾聽到得這麼像。
不管選擇去哪裡,成長好像被塑造成一個逐漸融入社會,接收、內化、再複製特定價值體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也慢慢地做出許多退讓,許多事情也再也不能自主。那種在體制裡不能夠自主選擇的幽閉感,是多數時候我對於人們大力讚揚的光環頭銜與璀璨未來感到懼怕的原因。過去幾年參加過許多學界與業界職涯規劃的工作坊,慢慢地感覺到我們普遍對於「成長」的認知時常建立在市場與資本主義的語彙上。我們談論「產出」、「效益」,講怎麼樣表現才能夠獲得體制的「認證」,我們被鼓勵勤奮工作、用力攫取,為的是證明自己有足夠的智識,事事講求技巧與策略。但是在這樣的成長邏輯下,到底什麼才是「足夠」呢?也許在資本化社會的眼光之下,沒有什麼是足夠的。所謂成長,還有伴隨而來得職業生涯,許多時候即建築在無盡的積累上:經驗、頭銜、產出、資本、認證等各式各樣的累積。無盡的積累帶領我們走向充滿人們注目的未來。
曾經是那麼渴望成長,渴望到有點迷失的地步,為了能夠茁壯即使犧牲健康快樂都無所謂的地步。直到這一兩年慢了下來,最近這陣子又更慢更慢,才開始想清楚一些事情:自己與體制的關係,還有生存,還有變成自己會厭惡或是欣賞的大人的可能。
在過去這半年所接觸的作品裡,發現幾位作家們不約而同地談論著成長與成熟這件事情,像是張曼娟描述成人步入中老年以後如何承擔照顧者的責任又能得宜自處,或是邱妙津在日記裡寫到她對於異性資本邏輯形塑的未來的憂懼感,還有李維菁討論女孩變成女人時對於性與身體的自愛與厭惡。雖然作家們所著眼的階段與面向非常不同,但她們都談論到個體的養成與社會涵化力的拉扯,好像一不小心,「我」就會消失,變成下一個資本與市場所企求的同化商品。
待在家裡的每一天,我時常回想許多過往經驗,童年的、最近的。如果我終將變成夢裡從背後上前擁抱一位女孩的大人,我希望當女孩轉身看見我的時候,我會是她欣賞、想要成為的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