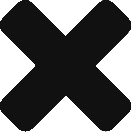在防疫旅館的第一個晚上,我拍了窗外的街景,跟系上的好友M分享。照片裡是我從位在二樓的房間看見的廣州街夜市,各式的招牌、霓虹燈,還有遊戲機台上不斷閃爍著的彩色光芒幾乎每個傍晚都準時地點亮街道。週末川流的人群,還有不分平日與週末都坐在大雨傘下等待生意上門的攤販,或是叼根香菸,或是與街坊鄰居攀談,是窗外自有的時序與生活。

窗內,M回傳簡訊說她真的很想念人群,還有疫情前能夠毫無忌諱讓自己身處人群的時光。 我知道自己能夠回來台灣很幸運,心裡也覺得很歉疚挑了一個不是那麼好的時機離開賓州,好像暫時放下了那裡的好友們,很多事情不能夠幫忙,也無法承諾。賓州的冬天又暗又長,還沒有五點天就全黑了,冰冷的日子會持續到明年五月,漫長的冬天就是一個想盡辦法抵抗季節性憂鬱與維生素D缺乏的時節。朋友L在郵件裡跟我開玩笑説,如果我是妳就在台灣待到冬天結束了再回來。 離開的時候,身邊的幾位好友都處在很艱難的階段,無論是身心健康還是職涯選擇都因為美國疫情失控而失序,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從原本的生命軌道被劇烈地拋擲出來。我最想念的是與好友們每週的散步,在秋天的颯爽還沒結束時享受最後的午後暖陽,有種在體制殘破的廢墟裡擁抱取暖的感覺。
而我也還沒有離開他們。關在旅館房間內隔離是很奇妙的經驗,把在賓州中斷的工作帶回來做,持續與在那裡的朋友們聯繫,講垃圾話、曬曬貓咪的照片,好像處在一個於時空中懸空的膠囊裡,即使換了時區與地景,卻感覺不到自己實際上已經在台北。好像一隻腳還踩在那天下午與好友散步時經過的落葉堆裡,另一隻腳卻在某個清晨踏進了充滿了亞熱帶濕氣的桃園機場,身體懸在中間,在一個封閉的、小小的房間裡,努力縮小兩腳之間的距離。
調時差的那幾天,我總是清晨五點多就醒來,拉開窗簾望一眼外邊的世界。天還未亮的廣州街上,總有幾名穿著螢光背心的清道夫,拉著垃圾桶與拖車,竹掃帚摩挲著柏油馬路。我聽不見他們的低語談話,卻聽沙沙作響的掃帚摻合著生鏽拖車的鏘鎯聲,悄悄地啟動清晨的廣州街。
喜歡這樣聆聽外面世界的聲音。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時空膠囊裡,我與窗外的世界的連結大抵來自城市所產生的聲音。許多時候,我沒有將窗簾拉開,因為我的正對面就是一排住家公寓,樓下就是夜市攤販,總是不習慣讓人近距離地看見我。這樣的不安感一方面來自於以前在台北的住家對面時常有一位中年男子站在樓梯間緊盯著我們家的客廳看,有一次甚至隔著街對著坐在客廳看電視的我自慰,那種被暴露在男性視角下的恐懼就這樣烙印在我的身體裡。想拉起窗簾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落腳的旅館有公開自己作為防疫旅館的資訊,行進廣州街的居民、來逛夜市的群眾大部分都戴著口罩,我不時擔心自己作為隔離檢疫者的身影,好像會讓窗外的人感到不安。我就這樣偶爾倚著窗簾,看一眼淺淺淡淡的藍天,看馬路斜對面仁濟醫院風中搖曳的椰子樹,對街的愛玉冰、甜不辣,還有樓下的芳香按摩館前駐足聊天的小販。大部分的時候,我聽著外面的聲音。
每天下午,廣州街上的攤商們陸陸續續地出現,一排排的打彈珠台被攤販們運送進鋪著地磚的街口,聽到拖車的鏘鎯聲以及機台碰撞地板的聲音,就知道快要三點了。從那個時候開始,小彈珠在機台裡碰撞滾動的聲音會持續至深夜。一週又屬星期六的夜市人潮最多,興奮的孩童一個個坐在彈珠台前,使勁地拉著把手,彈珠乒砰撞擊,雜合著傍晚的街坊廣播測試。週末的下午六點,廣州街有夜市廣播,正式宣布夜市營業開始。廣播裡頭傳來的,是一個年輕的男聲,悅耳平穩,以中英日三語正式地為夜市拉開序幕。週末傍晚的夜市就是如此熱鬧,窗外的街道上,嘈雜的人聲與摩托車聲作為背景,應和著到午夜都不間斷滾動的彈珠,偶爾再堆疊著不知道哪裡傳來的以薩克斯風演奏的望春風,好像這些就是廣州街夜市呼吸的節奏一樣。
以前總是習慣以視覺去了解這個世界,又因為平時的工作仰賴閱讀,很少認真思考自己與周遭的聲音的關係,或是該如何透過聲音去觀察自己所處的世界。直到幾年前遇見做聲音研究的好友S,才漸漸體會了聲音作為媒介生發出的故事與政治。S告訴我,探討聲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去理解某個特定的聲音是在什麼樣的時空情境,以什麼樣的方式被製造出來的。她跟我舉了歌劇演員的例子,說要能夠發出渾厚高亢的聲音,歌劇演員除了經過嚴苛的訓練外,身形也被聲樂訓練形塑成特定的樣子,讓身體裡的臟器與組織達到最大的共鳴發聲。S還跟我說了中國八零年代的流行音樂,說哪些歌手的唱腔會被認定為是左派或是右派唱法,而這樣的認定邏輯背後也安藏著人們對於聲音、唱腔的特定預設。
我聽S講聲音聽得津津有味,也是從那時候起,我開始對周遭的聲音,無論是人聲或是非人聲,還有各式被貼上標籤的口音有所留意。無形的聲音所牽引出的其實是產生聲音的身體、環境、器物,還有這一些身體與物事在產出聲音時所需要的勞動與時間。有的聲音象徵著權力與辨識度,容易被人們聽見、被認同,佔據了日常聲音地景的許多空間。有的聲音細微含糊,在嘈雜聲音頻道的間隙裡,卑微地存在著,卻代表著日常生活中最真實也不可獲缺的面貌。
雖然一個人關在房內,但是通過聲音,還是能與外界有所連接。過去的15天內,每一天的三餐時間都有旅館櫃檯打來的電話,告知隔離的房客餐點就在門外。我聽見了電話那一頭四個不同的聲音:帶有娃娃音的年輕女聲,吞吐緩慢的中年聲調,平穩低沉的男聲,還有一個聲音表情非常愉悅輕巧的聲音。除此之外,還有每一天與我通話兩次確認我健康狀況的區公所幹事,那是一個有朝氣的可愛女聲。打著這些字的時候,窗外傳來組裝彈珠台與遮雨棚的聲音,傘骨與鋼筋摩擦著地板,搭建起架子,搭建起生活。
聆聽這些聲音,窗外的與窗內的,暫時在一個瘋狂暴亂的世界中找到了舒心的音頻。也是因為聆聽了,更想仔細地頻藉著聲音的形狀去想像這些聲音背後所代表的勞力與時間。這麼多人都在為了生存與生活努力,或是架起彈珠台,或是打客服電話,建構起疫情時代中持續讓生活得以持續的網絡。而自己在這樣網絡裡安靜無聲地處著,在小房間裡諦聽網絡裡的聲音與共振,惦記著產生這些聲音所需要的情感與身體勞動,讓它暫時托著漂浮在疫情時代時而無所適從的自己。